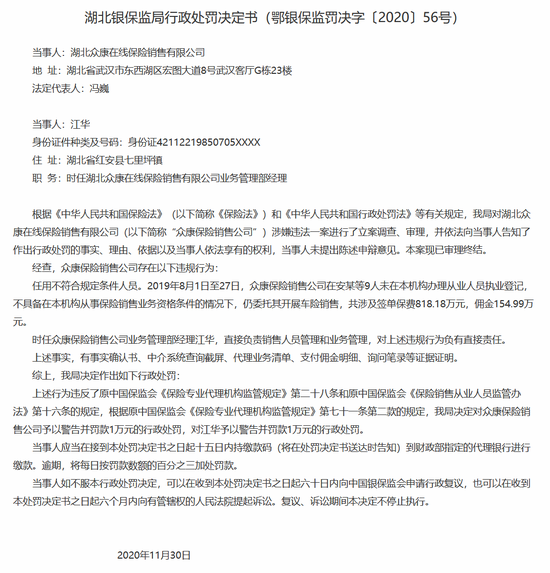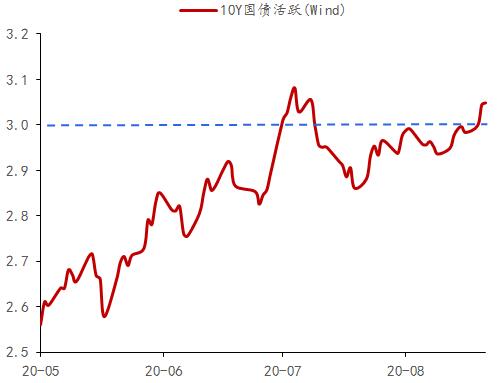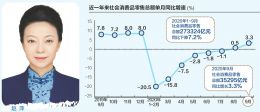曹远征(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区别于理论学家,在市场一线的经济学家担任的是航海瞭望手的角色。这不仅要求经济学家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更要求其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可加以分析和预判。由此,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在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行动依据的同时,亦可为宏观经济活动提供决策支持。
一
《温故知新——洞察经济金融潮汐》第一篇就是以宏观经济与政策为名,由作者多年来宏观经济分析汇集而成,并因这一汇集,展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轮廓。根据作者的连续观察,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表现为在波动中不断下行的态势,并且波峰波谷差异明显变小,使经济下行具有了平滑性。显然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统计,在过去20年,中国GDP增速由两位数以上逐渐波动下滑到目前的6%多一点,而且过去热议的经济周期也基本不显现了,至少出现了变形。
这一观察引发了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是波动。经济无疑是具有波动性的,并因连续的波动形成可以观测到波幅和波长基本稳定的周期。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波动似乎不再是原有周期的重复,出现了变形。那么,变形是出现在波幅上还是在波长上?抑或是兼而有之?原因是什么?第二是趋势。经济增长无疑是有趋势的。这一趋势的形成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性原因所致。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似乎不再沿着以往的轨道前行,增长不再加速或持平,而开始持续性下行。那么,造成这种新趋势的结构性变化是什么?原因何在?十分明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预判未来的关键,成为潮汐需要洞察的理由。
早在2013年,作者就发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建立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收入本篇的《中国经济: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找平衡》一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从短期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步伐放缓,同时,侧重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导致中国经济波动性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增长”是必要的。但是,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下行并不完全归结于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需求的波动,尽管当前的中国经济下行有“三驾马车”同步放缓的因素,但还有深藏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原因。作者指出,“从供给侧结构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一半。”“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多产业盲目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供给和需求的结构的不对称是经济波动加大并持续下行的基本原因。于是,对经济政策而言,寻求对称性成为问题的重心,而结构调整成为努力的方向,目标是引领在短期上表现为对付经济下滑幅度过大的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长期上表现为引领结构变化的制度性安排。其中深化体制改革十分重要。作者认为“继续采取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刺激短期需求已经难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近忧和远虑问题。必须进行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红利,才能彻底解决当前困难和长远发展的平衡”。
二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从供需对称性入手,通过改革来寻找平衡的分析框架是有理论解释力的。经济学认为,供给结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从而是个长期缓慢的变动过程。在供给结构短期稳定的情况下,经济的波动是由需求的变动引起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以产品过剩为代表的产能过剩,并周而复始,呈现出波峰波谷之间各阶段特征明显且波长基本一致的周期律,并可观测。稳定的周期因之成为分析宏观经济表现的基础,进而发展成为趋势外推的成熟预测方法。但是如果出现持续性的产能过剩,则意味着供给结构长期不能响应需求的变化,致使经济周期出现了变形,波峰波谷之间的阶段特征模糊且波长与以往明显不一致。这时旨在提升总需求的需求侧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至多能稳定增长,使波峰尤其波谷得以熨平,而不能改变趋势。换言之,若要改变趋势则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由于结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而技术进步又是随机的,从而难以把握其进步的方向。这也构成经济学为什么很少讨论供给侧的原因。历史上所形成的供给侧结构调整政策,例如产业政策都是建立在大规模主流工业技术基础之上的。因主流而可预期,因大规模而实用。由此,在技术进步方向尚不可预期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改革改善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即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在改善供需对称性的前提下,重塑引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换言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单纯依赖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或行政手段来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是有效的选择。
三
这一有别于传统的基于周期的趋势外推的分析框架,在解释过往经济变化的同时,也增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事实上,自2013年起,中国的经济及经济政策发生了符合该分析框架的预期变化。
首先,在短期宏观经济表现的调控中,由于总需求波动是经济周期的原因需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熨平波动,而由于客观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管理是在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作权衡并相机处理。中国的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体现了这一原则,但其操作目标和方式却有了创新。不仅反映为需求侧的“保增长”,而且建立了调控区间。这一区间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在官方文件中未明示这一区间的上下限,但从实践来看,其上限是以CPI表达的通货膨胀不高于5%,其下限是以调查失业率曲线表达的充分就业也不高于5%。其管理目标是:在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即CPI指标不超过5% 的情况下,盯住经济下滑的态势,避免其滑出下限,即调查失业率不高于5%;其管理的方式是采用预调、微调的办法,提前预判,小剂量提供,频繁从事。这种政策的指向,显然不同于一味拉升经济增长的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在尊重结构性变化趋势基础上的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安排,既熨平了波动,又不僵化,根据结构性变化趋势使调控区间缓慢下移。从长期角度观察,其效果是明显的。自2012年开始,中国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就开始下降,每年下降约300万人。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开始首次超过工业,而服务业有更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共同预示充分就业压力的减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数的下降。因此,要使宏观调控区间的下限在自然下移的同时也不出现就业的困难。
其次,在需求侧“保增长”是宏观经济表现稳定的条件下,加大了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力度。2015年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它包括两个方面“去”和“补”。在“去”中又把“去产能”置于优先位置。当时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冶金、煤炭、水泥、化工等领域。这些都属于大规模生产的主流工业技术,其调整的方向有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可用产业政策乃至行政手段加以实施。在钢铁领域是宝钢和武钢的合并,用行政手段去产能;在水泥和有色金属及煤炭领域,则是在产业政策指导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所谓产业政策是明确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通常要求行业前十名集中市场份额的60%以上,并在规定时间完成。而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则遵循市场原则自由结合;在“补”中,又把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在内的创新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通过“营改增”,降低了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性企业的经营成本,激励了“万众创业”的热情,使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另一方面,通过诸如信用贷款、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服务业无论增加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快速上升,2019年已占GDP的53.9%。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中国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深刻转变。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改革。只有通过改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才能改善供给对需求的响应程度与速度。这一改革指向必然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启动了60条、300多项改革措施,不仅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随着“五位一体”全面深化和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已初见端倪。
由上可知,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不仅说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而且表明其有预测能力,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区别于基于周期波动的“新周期”分析框架,更贴近历史的进程。基于中国经济实际的,以改革为中心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短中长政策组合,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指出的“改革是实现保增长与调整结构平衡的根本途径”发挥了积极作用,符合作者预期,成就了今日中国面向现代化,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新局面。
(本文为作者为《温故知新——洞察经济金融潮汐》一书所做的序,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