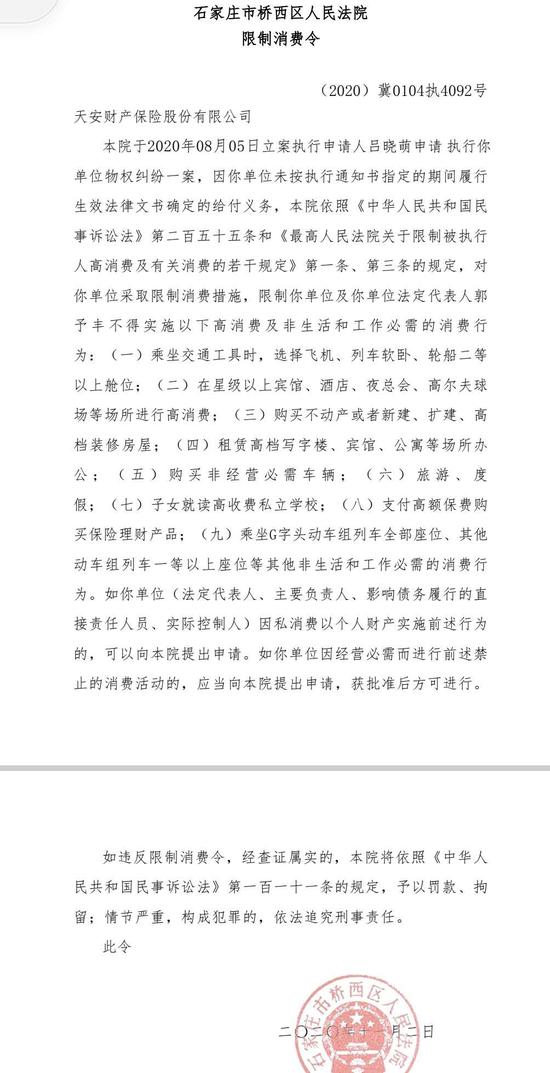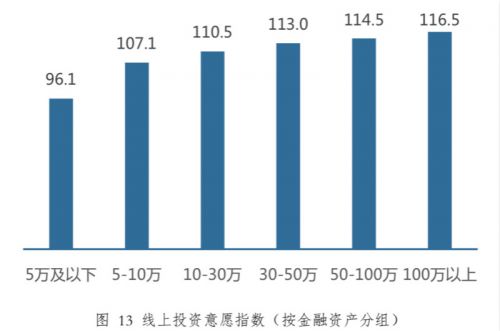(萨尔斯堡莫扎特塑像 图片来源:IC Photo)
乐正禾/文
梅纳德·所罗门的《莫扎特传》原版副标题为“Alife”,644页厚的中文版沉甸甸的,对许多中国音乐爱好者而言,它的分量其实还远不止于此毕竟他的《贝多芬传》珠玉在前,风靡于国内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之间。
从1970年代后期初稿的《贝多芬传》,到1995年的莫扎特传记,拥有心理学行医执照的所罗门一以贯之地以精神分析作为重要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揣测两位音乐巨匠人生中种种的谜团。相比解决了贝多芬书信中“永恒爱人”确切身份等诸多生平问题的《贝多芬传》,《莫扎特传》使用精神分析工具更加大胆一些,其延伸也更加悠远。因此必然会在音乐学界兴起比《贝多芬传》更大的争议。
两部巨著中的贝多芬与莫扎特
《文明的进程》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曾以社会学角度探讨沃尔夫冈·莫扎特的成功或失败。他在比较“同为自由音乐家的贝多芬和莫扎特”时,曾表示:“(关于音乐想象力)当贝多芬开始突破传统时,莫扎特只能在古老的标准和框架里发展个体的可能性。”社会学者依靠观察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的研究来诠释音乐家时,从来都有一个固定的缺陷:不得不以贝多芬与莫扎特在艺术开辟上的既有评价为前提,再寻求事后解释。然而问题在于,艺术风格史并不是简单事实判断的历史,当然更不是价值判断的产物,而是审美判断的总和。人们在现实中经常混淆这些。有时看似以事实为准绳,其实只是将事实屈就于价值;或是以为自己在捍卫一个价值,但那明明是一个审美的偏见;但反过来讲:假如命令一个算力强大的AI机器去书写艺术风格史,那必然生出一个令人惊鄂万分又啼笑皆非的体系和结论,因为它的标准明确,论证也“太正确了”,而非本该形成的“存有偏见的产物”。曾有研究者怀着沮丧的心情将既有的音乐理论归为“唯象的理论体系“。其实即使真的“唯象”,又如何呢?
也许当精神分析论者和音乐学者结合于一人之身时,未尝不能产生奇妙的火花。他们至少不会放弃以被研究者的主观为出发点。我们强调,以观察个体、群体的行为来阐释音乐有时会形成荒谬。所幸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宣扬外部事件和行为逻辑能直接酝酿出某个好的音乐作品了某君目睹了不平事,他从而创作了“激于义愤的音乐”。在某些特殊的年代人们会相信这些,但现今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假如他为此写出精彩的社会评论那是可能的,若是音乐的话至少很难是很精彩且流芳千古的作品。然而,精神甚至肉体的欢愉,家庭的创伤,反而可能令艺术作品破土而出,即使包裹它的外壳可能是社会价值,甚至是权威下的应制之作。肖斯塔科维奇这类作曲家的作品与生涯,也许就能体现这一点。在多数人视精神分析理论为“须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下,所罗门版《莫扎特传》和《贝多芬传》更加专注于人物内心世界显得自有其意义。
实际上,所罗门并不是对社会层面无所顾忌,两部传记皆是心理和社会平衡的产物,但所罗门把社会层面的介绍仅作为探究人物内心世界合理性的现实保障。以贝多芬的人生为例:为了在一个比拼琴技为大,寻求赞助为基本的环境中立足,他不得不选择“与歌唱性相对”的倾向去成就自己前期半数以上的钢琴奏鸣曲,但他之所以由早期李斯特式键盘炫技者转身为伟大的沉思性艺术创造者,却缘于深恐耳疾被公开而不得不远离人群的现实(哪怕初期听力折损并不大,但耳鸣带来的不适感和对未来预期的恐惧感才是更重要的),对贝多芬而言,英雄性和交响性正是自此而生的,诱发它的与其说是勇气,不如说根本在于恐惧和恐惧伴生的自我对抗。晚期的贝多芬风格则意味着一个早已习惯和恐惧(比如对亲人抚养权随时可能被剥夺的恐惧)共处的老人。
相比而言,莫扎特歌唱性部分的本源也是来源于社会的,作为庆典和欢乐场合的小夜曲先天具有愉悦的功能,莫扎特也正是被父亲利奥波德当作自己的纯粹工具,从事着许多“愉悦他人”的早年活动。
也许人们印象中莫扎特音乐中许多令人欢愉的美,实则对应了利奥波德的“胁迫”下,莫扎特“利他”的部分。而所罗门在《莫扎特传》中,为我们展示着这种以愉悦他人而作的模仿。前期的莫扎特似乎在模仿一切走红的创作者的风格,从而取悦欧洲各国、各地、各宫廷甚至各个剧场口味不同的听众。笔者在某篇文章比较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段落中曾说“莫扎特的模仿期并不长”,所谓“不长的模仿期”所指为纯粹学习性的模仿,但莫札特的模仿是纯粹运用性的模仿,那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反而是超脱的音乐语法和创作习惯。正因如此,莫扎特形成了许多人想象中的“没有风格的风格”,甚至“上帝般的风格”。
莫扎特的作品为我们带来他在遥远时空中的“无私而利他的意象”哪怕在他的年代,这其实都是有报酬的。但我们又无法欺骗自己,就如同现实中人们对莫扎特神秘而矛盾的观感:莫扎特的音乐是令人愉悦的;莫扎特的音乐似乎又是黑暗的。这种黑暗和悲剧性绝不仅仅存在于其庞大作品宝库中的边边角角,甚至在最知名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中也有体现。莫扎特的音乐习惯于在娱人的欢愉后从容地过渡到一个幽暗无比,又或是充满自我宽慰的世界,其格调哀而不怨。莫扎特的“利他”和“黑暗”和他面对的家庭关系似乎有所关联。
两对父子
历史上多数莫扎特问题的论述者都对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采取了认可的基本态度,区别仅在于是否“有所保留的认可”。身为剧作家的希尔德斯海姆(W·Hildesheimer)在专著《莫扎特论》中做出的基本判断是“他(利奥波德)的思想和计划都是为了儿子,他巨大的失望、提防、断念都是为了儿子”。利奥波德的行为被盖以“迂腐却又长远聪明”的结论,听来很是矛盾。希尔德斯海姆确实发现了莫扎特人生中戏剧性的重要节点,但他无奈的将其归咎于利奥波德的“虚荣”。
但所罗门不希望止步于提出一个戏剧性的节点,在所罗门的观察下,父子详实的书信往来资料可以提供莫扎特和利奥波德双方的精神分析空间。父亲利奥波德铸造了一个严密的“利奥波德沃尔夫冈”父子心理共生体,利奥波德的成功就是这个共生体的成功,但作为工具的沃尔夫冈的成功,竟然不被视为这个共生体的成功。所罗门的精神分析框架也许值得谨慎看待,但他确实努力解释了利奥波德的行为逻辑何以矛盾重重,而莫扎特的痛苦则在于自己必须冲破这个被父亲坚决保护的共生逻辑。但无奈的是,莫扎特对父亲私心的反抗却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
通读所罗门的两部传记著作,我们发现“利奥波德沃尔夫冈”这个共生体所谓的成功,竟然诱发了贝多芬最初的悲剧根源:作为歌唱家的贝多芬父亲,正是垂涎于莫扎特父子的”成功“,而成为一位键盘演奏教学水平蹩脚的暴君式的父亲。没有这样的经历,贝多芬抵抗父权以强烈自我塑造为标志的音乐性格就无法最终产生。对比之下,利奥波德-沃尔夫冈”共生体的“成功”,塑造了集欢愉、幽暗于一身的莫扎特音乐,反之,”约翰-路德维希“共生体的提早破产则使得在多年后的苦难激发下,英雄的贝多芬音乐破土而出……
所罗门这种对内心的探究可以和艺术作品本身产生共鸣,莫扎特对父权的纠结和妥协,构成了他对母亲过世的负罪感(所罗门认为利奥波特通过加重莫扎特对母亲过世莫须有的责任,而强化对儿子的精神控制)。每当笔者听到莫扎特丧母期间完成的《E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作品K304号)的小步舞曲乐章时,都对何样的初速能表达“莫扎特对母亲的怀恋”踌躇不已,按照音乐旋律的节奏、步调来说,过慢的初速肯定是不算特别合适的,但中庸或过快的速度又消解了伤感的乐思。但所罗门的精神分析令笔者忽然恍然大悟,也许萌生它的并不是伤感,而是自我宽慰。也就是说只要乐曲中段的三声中部部分处理得当,能够表达这种宽慰,那才是最重要的。所罗门的分析进而希望打破我们因从贝多芬时代回看,而对古典主义持有的刻板定见。慢乐章也许并不总是用于沉思的跳板,行板和柔板乐章在莫扎特的世界中往往是整部作品的最中心位置的内核部分。
也许,所罗门的精神分析貌似离经叛道,实则反倒是小心翼翼的。由精神分析出发而非从社会现实出发的音乐诠释其实是谨慎,而非激进的。在对莫扎特父子内心世界的观察中,所罗门的视野并不以宽广突破见长,和他比较,查尔斯·罗森在《古典风格》中仅仅在对海顿的分期方式,就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大胆而开阔的音乐史视野(莫扎特死前的海顿作为一大章,莫扎特死后的海顿作为另一大章)。但反而是所罗门认为罗森对《降B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K174号)评价“过于惊人”,他甚至用激动到大惊小怪的态度面对罗森判断莫扎特最善以音响展现肉体欢愉、纵欲、“对感伤价值的摧毁“的大胆表达。所罗门由此声称罗森是“简洁而雄辩的”。
传记的价值
我们为什么要研读音乐家的传记呢?我们和音乐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对不少的音乐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音乐家传记最为基础的功能之一,其实是艺术家浩瀚音乐作品的“编年”标示了我们心爱的曲目在作者艺术生涯轨迹中的位置。
这也是为何笔者喜欢说: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其实是一部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时代的文学性怀念,而所罗门的两部传记,或者金德曼的《贝多芬》才是艺术家的传记。莫扎特的“作品编年”在许久前被路德维希·冯·克歇尔呕心沥血而成的作品编号组织出了骨架,而所罗门对莫扎特父子,对贝多芬的内心探究则不仅为我们铸造了更丰富的血肉,且揣测出二者平凡而又不凡的心灵。
所罗门似乎也在告诫我们:虽然用脱离社会环境的妄想错误衡量历史人物,会形成“何不食肉糜”的判断,但我们浑然不知自己虽逃脱社会层面的“何不食肉糜”,却坠入了精神层面的“何不食肉糜”之中。因此才会以物质和社会层面的对比得出“贝多芬的人生比莫扎特更加不幸”的结论。
从1970年代初稿的《贝多芬传》,到1990年代写就的《莫扎特传》,中国读者继续期待着所罗门在21世纪成就的那部反映晚期贝多芬的著作能够中文化,并以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总结。所罗门先生在2020年这一苦难的年份仙逝而去,这一年同时也是贝多芬的250年诞辰,我们送走了贝多芬出世的大年,转眼又将迎来莫扎特逝去的小年(1791-2021),阅读所罗门的两部传记著作,也许会是对他和这两位音乐大师不错的纪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