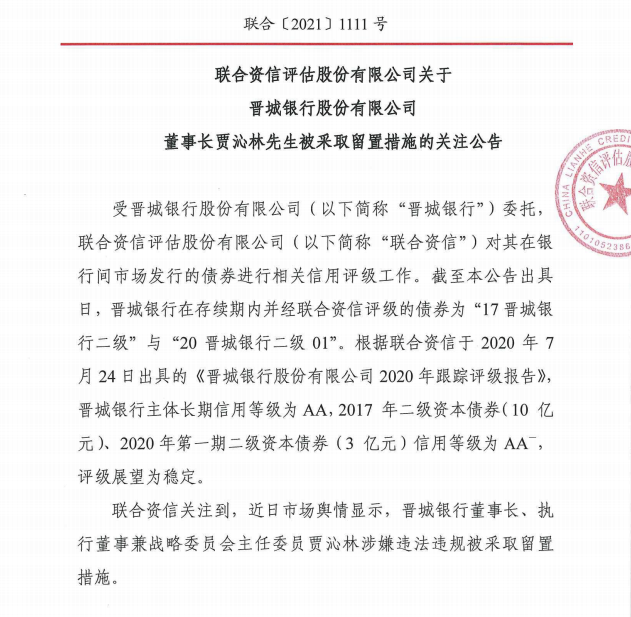(图片来源:IC Photo)
陈永伟/文
最近一段时间,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又一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和前几年不同,这次人们关于这些新经济形式的讨论,焦点已经从“它们能不能更好促进资源分配”、“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转移到了“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经济形式中平台和劳动者关系”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上。
这场舆论热点的起源是两次“卧底”:先是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的半天外卖“卧底”。这场历时12小时,收入41元的体验,以一种十分直观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作为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代表的外卖小哥群体的艰辛。然后就是北大博士陈龙的那篇刷屏论文。在论文中,陈博士以自己半年“卧底”外卖配送的经历,向人们全景式地展示了平台是如何应用算法对劳动者实施“数字控制”,从而让原本灵活就业的人们一步步陷入内卷的。
在这两场“卧底”之后,更多关于平台和劳动者关系的报道陆续涌现。人们开始看到,部分平台是如何在用算法加强对劳动者控制的同时,努力回避着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福利和保障。而那些在平台监控之下努力劳动的人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竟然是在完全没有社保的情况下“裸奔”。更为让人沮丧的是,随着内卷程度的逐步加深,他们似乎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平台,因为长期在平台上从事低技能劳动而得不到技能训练,已经让他们失去了选择其他就业岗位的能力……
随着这些报道的不断增多,一些情绪化的言论也开始在网上出现。很多人大骂资本的黑心,痛斥平台对劳动者的剥削。也有人呼吁,干脆取缔平台灵活用工这种形式,让所有平台都把平台上的劳动者当成正式员工来对待,给予他们正式员工的所有福利和保障。
作为一个平台研究者,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在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中,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现实当中,不少平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得非常不够,社会上很多关于平台的指责也确有其道理。但简单地把所有问题都归于资本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要求取消新的经济形式,或者完全用现有的规则来一刀切地处理新问题,似乎也不现实。
事实上,在现在这种社会面临经济转型,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等新的就业形式还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阀”。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灵活就业的人数已经达2亿左右。在这2亿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等新的就业形式。如果我们简单地否定了这些就业形式,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各种问题当然就不复存在了,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可能要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在这种背景之下,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可能是要设立一套平衡平台和劳动者关系的规则,为劳动者争得最为需要的权利。与此同时,还应该综合动员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探索一套能够更好支持各种新就业形式发展的制度,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其中的两点:如何探索平台用工的保障,以及如何安排平台用工的技能培训。
搞清身份,弄明权益
在现阶段,关于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问题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对这批就业人员“身份”争议的一个方面。在我国,传统上认可的企业与其使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劳动关系,一种是劳务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下,劳动者是企业的成员,需要服从企业的管理,与此同时,企业则需要对其支付报酬,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和福利。而在劳务关系之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则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劳动者为企业提供劳动,企业向其提供报酬,但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不必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和福利。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两种关系分别对应的其实就是科斯所讲的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企业与市场的具象化,劳动关系体现的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而劳务关系则是企业参与的一种市场交易,只不过购买的产品是劳动服务。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这种“二分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可以很容易地对应到这两种情况中,然后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决定是否应该对劳动者提供福利和保障、提供怎样的福利和保障。
但是随着平台的兴起,这种“二分法”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从性质上讲,平台是具有“二重性”的,它既是一个企业,又是一个市场。
从对劳动者的组织和控制上讲,它并不像传统企业那样具有明确的强制性,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参加多少时间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者和平台企业的关系比较像是在市场上进行劳务交易的双方。但与此同时,在劳动者提供劳动时,平台企业又可能对劳动者进行很强的控制。例如,陈龙博士论文中提到的平台通过算法对外卖小哥进行的控制,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中企业老板对其员工的控制力度。从这个角度看,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又更加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由于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就导致对平台上劳动者的身份很难准确认定。而正是由于这种身份的难以确定,就给了平台规避为劳动者提供福利保障的理由。
在操作上,很多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会明确自己对劳动者的使用是通过某个第三方的中介公司实现的,这就在法律上坐实了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务关系。而既然是劳务关系,那么平台就当然可以拒绝提供像“五险一金”这样的保障和福利。不仅如此,如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事故,产生了损失,平台也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规避责任。近年来,曾曝出过好几起外卖小哥在配送途中发生意外的新闻,最终平台方面基本都没有承担责任,其理论基础就在于此。
从直观上看,平台的这种完全甩锅当然是不合理,也是不厚道的。但如果问一问平台,他们似乎也有自己的道理毕竟,平台不会像传统企业那样对员工的工作时间有明确的要求,有的人工作时间很长,但有的可能只是注册在案,基本不工作。如果要让平台都和传统企业一样,为在它上面工作的劳动者提供“五险一金”等保障,那岂不是给了很多人套利空间,吸引他们为了骗取保障而来平台注册挂名。
考虑到以上情况,尽快明确平台上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明确平台应该对其提供的保障和福利,就成了当务之急。要达到这个目标,比较有代表性的思路有两种:
一种思路是,把平台的灵活用工独立地定义为一种新的关系,对这种关系下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新的界定。从全球范围看,现在不少国家采用了这个思路。例如,英国、德国、加拿大就分别把在平台灵活就业的人员定义为了“非雇员劳动者”、“类雇员”和“非独立承包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平台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另一种思路则是,依然沿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二分的思路,建立一套标准,根据具体情况把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划入到这两种关系中,然后根据不同的关系,要求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不同的福利。
在两种思路中,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思路从长远看是更为合理的。因为在平台条件下,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确实和过去有很大不同,因而确立一种新的关系,或许是更为合适的。但要执行这种思路,会涉及对法律进行修改,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考虑到现实情况,可以考虑先根据第二种思路,把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放到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分类和思考。
在进行具体的操作时,我们或许可以借助经济学中的相关知识来辅助判断。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经济学维度上看,其实是企业与市场关系的体现。而在科斯的相关理论中,区分企业与市场的重要关系是所谓的“控制力”。也就是说,如果在交互当中,甲方对乙方有很强控制力,而乙方对甲方的依赖性很强,那么甲乙双方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企业内部的层级关系;反之,如果甲方对乙方没有控制力,而乙方也不依赖于甲方,那么甲乙双方就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劳务提供关系。
在执行上述思路时,我们可以构造一些用来刻画平台“控制力”强弱的指标体系,例如“劳动者是否可以自主定价”、“平台是否直接控制和指导服务”、“平台是否有监督评价机制”、“劳动者的收入中,平台劳动占比有多大”、“劳动者的总劳动时间中,在平台劳动时间的比例有多高”等,每个项目分别设立一定的分值。按照对于每个岗位、每个劳动者的具体得分状况,来对平台和劳动者的关系进行认定。
这样,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些工作时间主要是送外卖、劳动收入主要来自于平台、工作时接受平台严格监督的外卖小哥应该被划为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平台应该为其提供“五险一金”等保障和福利;而那些只是利用一些业余时间在平台兼个职,主要收入也不来自于此的人员,则应该是劳务关系,平台自然也没有为其提供相应保障的义务。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只是“企业-市场”光谱的两端。如果我们建立了以上所说的指标体系,就可以找到每一个具体的工作在光谱上对应的位置。如果以后我们通过修法,提出了新的关系,也可以很容易地在光谱上找到这种关系的某个对应点,然后按图索骥地找到企业应该提供哪些保障、劳动者可以享受什么保障。
把一些权益先保障起来
除了对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进行明确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考虑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一些变更。
目前,很多平台不愿意承认劳动者与自己是劳动关系,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旦它们认定了这种关系,就必须付出很大的一笔成本。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企业必须要为员工提供社保“五险”。(注:近年,生育保险与职工医保进行了合并实施,因此一些报道提法为“四险”。但考虑到这两者只是合并实施,生育保险事实上仍然存在,因此这里仍沿用“五险”的提法)这五险是强制的,也不能分开提供,因此从企业角度看,其成本就比较高。
应该说,平台企业出于规避支出的角度考虑,想回避劳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保开支,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对于社保的购买意愿也非常低。有不少零工经济的从业者收入并不低,按理说,即使平台企业不为他们购买社保,他们也是有能力自行办理的。但从现实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这么做。
就以外卖小哥为例,前几年我曾和一位社会学研究者一起访谈过几十位小哥。在我们访谈的样本当中,平均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五千多,做的好的,一个月七八千的也不少。如果单纯从收入上看,他们中的不少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当时北京的平均工资。但在这些小哥中,却很少有想到为自己去办理社保的。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人称“单王”的小哥。他跑单很勤快,一天能跑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下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万三千多,可以说是相当可观了,但他也同样没有办社保。我问他,为什么不办呢?他对我嘿嘿笑了笑,说:“过几年还指不定上哪个城市去混呢。浪费这个钱干什么?还不如拿现钱,实在!”应该说,这位“单王”说的话虽然朴实,但却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很多劳动者眼里,社保其实并不是那么必须的。
有很多人听到这种观点,就认为这些劳动者是短视的,不理性的。但事实上,他们在做出不办社保的决策时,是相当理性,经过比较的。一般来说,这部分人群都相对年轻,身体还比较健康,得病的概率相对较小,因此用到医疗保险的概率确实不大。至于养老险,他们离退休时间还很长,所以暂时也不需要。而且,现在各种形势变化都很快,未来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到时候自己还在不在当前城市,养老金的政策又会是怎样,其实都不确定。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和单位有劳动关系的传统型就业者来说,他们的社保还有很多附带的属性。例如,很多地方规定落户、购房,以及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都要有一定的年限。但对于很多平台的灵活就业者来说,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诉求,很可能今天在城市打工,明天就回老家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办理社保确实就可能是一个个人理性的选择。
既然平台企业不想给劳动者办社保,劳动者本身也可能没有意愿,那么如果强行规定劳动关系就要购买完整的“五险”,结果很可能是平台与劳动者之间达成合谋,以某种方式共同回避掉这一“负担”。
从现有的实践看,像外卖小哥、司机等群体,工作强度大、危险也不小,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工作的平台,对于工伤险都有比较大的需求。但在现在这种“五险”必须一起办的情况下,这个最必须的险很可能被一起省掉。
应当承认,在传统环境下,把“五险”合并征收,是既有利于保障员工福利,也有助于简化企业工作的。但这个好制度在面对平台灵活就业时,却有些捉襟见肘。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考虑退而求其次,允许平台根据劳动者的情况,选择为其办理“五险”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类型,这样就可以把一些最应该有的保障先提供给劳动者。其余的问题,可以再在其基础上进行解决。
此外,考虑到平台灵活就业者在保障诉求上和传统企业的稳定就业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可以考虑专门为他们设计一些保障制度。如果国家出面设计不方便,也可以考虑引入一些社会资本,组织一些政府监督之下的商业保险项目,根据他们的确切诉求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现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创业项目,它们的实践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创新机制求解技能积累难题
除了保障问题外,另一个最近争议较多的问题是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技能积累和培训。一些观点认为,目前零工经济提供的岗位,例如外卖配送、网约车司机等,都是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些岗位之后,就可能陷入一种低技能的陷阱,从而失去了以后从事更高技能、更高报酬工作的可能。而从国家的角度看,随着零工经济的虹吸效应不断增大,很多传统的行业,如制造业就可能出现无人可用的局面,而这很可能对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带来比较负面的影响。在诸如“大家都去送外卖,制造业工人哪里来”、“送外卖的年轻人未来在哪里”等吸引眼球的标题之下,这个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应当承认,在当前的形势下,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技能问题确实需要重视,也十分值得探讨。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突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把灵活就业人员等同于低技能经济,或者把这种就业形态的发展和制造业或其他产业的发展对立起来,那就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了。
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平台灵活就业岗位是非常技术密集型的,其从业本身也是一种技能的积累。例如,现在有不少设计师是以零工的身份承接外包的设计工作,这些工作的技术含量并不比他们在传统岗位上所遇到的低,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业务能力提升也不会比在传统岗位上来得少。就算是快递员、司机等岗位,其实本身也有很多外界不知道的技能要求,而这些技能本身都是可以积累,并转移到其他行业的。现在很多地区已经推出了针对快递、司机等岗位的职称评定,其原因就在于此。倒是一些传统的岗位,如工业流水线,由于分工的细化,工人的工作已经变得非常机械化而缺乏技术含量。
至于说零工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发展,则是倒置了因果。事实上,之所以很多人离开了原有工作后,不再选择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岗位进行就业,而是选择了灵活就业,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从事新岗位所需要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旧产业衰退,以及这些产业的原从业者的技能难以匹配新行业催生了零工经济的繁荣,而不是零工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旧行业的没落。
在明白了以上问题后,我们就不难知道,所谓的“低技术陷阱”问题,其实是一个在技术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把这个问题全部推到平台,试图让平台来承担对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的责任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相比于以上的这个思路,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可能是“谁用工、谁培训”,也就是说,让潜在的用工单位提供培训,承担培训成本。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用工单位开出很高的工资,却招不到工的情况。从工作的性价比看,很多岗位其实要比灵活就业更有吸引力。但为什么这些待遇丰厚的工作却经常招不到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需求和劳动人员技能之间的不匹配。
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个不难解决的问题只要企业或劳动者当中有一方愿意承担培训的成本不就可以了吗?但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从劳动者的角度看,他们不愿意接受培训的原因:一是没钱。毕竟现在要报一个班学技术,学费动辄几千上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的。考虑到学习的时间,其总成本更高。二是怕学了后还是找不到合意的工作。在市场上,劳动者所拥有的信息经常是相对不足的,他们很难确切掌握市场供需的真实走向。一旦在接受培训后也无法找到工作,所有的成本就需要全由他们自己承担。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技术的迭代也很快,一个不小心,为学习某个技能而投入的金钱和精力就可能永远打了水漂。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例如,前几年市场上开始流行Python,很多培训机构为了炒作课程,都声称学了Python,月入就能轻松过万。在各种广告铺天盖地的轰炸之下,很多人真去学了Python。学完了才发现,市场上的Python编程人员早已供大于求,传说中月入过万的工作真是遍寻不得。正是在这种成本和信息的双重约束之下,很多劳动者才宁愿去从事技术门槛较低的灵活就业,而不愿意自己接受培训。
而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呢,他们不愿意培训员工专业技能,而更愿意招收已有技术的劳动者的原因也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成本其实很高。如果企业在招收员工之后进行培训,那么它所要承担的就不仅是简单的培训费,还要同时承担员工在参与培训期间的各项工资和福利。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阶段,员工还不能工作,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显然,这样的成本,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第二个原因是,自己培训出来的工人很可能被其他企业挖走。一个企业为了培训一个工人,需要花费不菲的投入。为了回收这些投入,不少企业会把这些成本摊到员工的工资中去,在一段时间内给员工发比较低的工资。如果在这个时候,别的企业如果开出一个比较高的工资,就很可能挖走这些员工。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现实中的企业大多也不愿意承担对新员工的培训。
那么,怎么才能打破上面这种困局呢?难道所谓的“低技能陷阱”真的无法破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要破解这个困局,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机制设计。在我看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在其著作《人工智能时代》里提出的一个思路可能是比较值得借鉴的。
卡普兰把这个方案叫做“工作培训抵押贷款”(vocational training loans)。具体来说,这个方案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列出一些需要的岗位目录,以及每个岗位所需要的人员。根据这个目录,企业可以先进行招聘。当找到了有工作意向的人,如果需要对他们进行岗位所需要的技术,他们可以给待培训的劳动者开具一个证明。劳动者可以拿着这个证明,以未来的工作收入为抵押,去银行进行贷款,并用这笔钱来进行对应的技术培训。当技术培训完成之后,他们可以回到招工的单位上班,赚取工资、偿还贷款。
通过这个简单的机制,就可以同时解决劳动者不愿意接受培训,以及企业招不到特定技术工人的问题。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是在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的情况下才进行培训的,并且是由企业出示了与岗位一一对应的证明,因此他们不怕在培训后找不到工作。而对于企业来讲,其所招的员工都会接受对应的培训,因而也非常适合其需要。
当然,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招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和企业达成就业意向时,还需要经过一定的培训时间,这可能对双方都造成一定的成本。为了弥补掉这部分成本,鼓励企业以这种方式进行招聘,政府可以采用一定的优惠政策,给予用这些方式招聘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劳动者的培训和技能积累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诚然,从很多方面看,卡普兰所指出的这个思路在细节方面还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但总体来讲,他确实为技术迅速变迁,技能折旧加速条件下,劳动者技能培训问题找到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对比简单地把这些问题推给可以给技能落后的劳动者提供过渡和保障的平台,倒不如顺着这个思路,找出一些切实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让劳动者更有尊严感、更有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