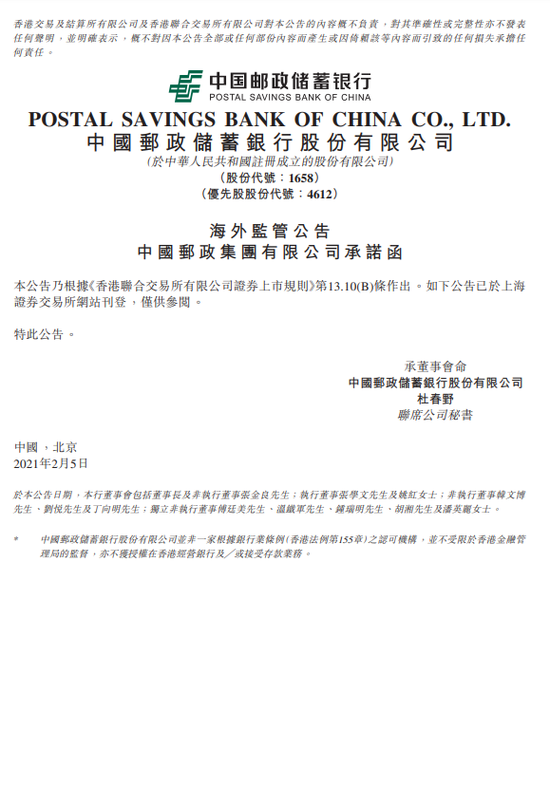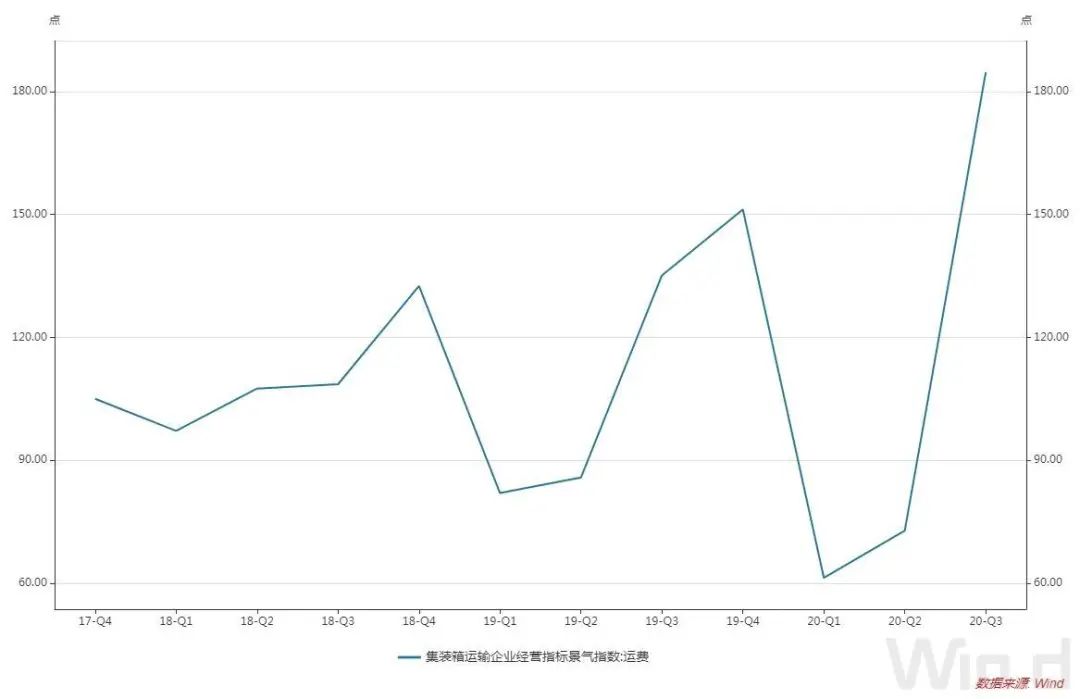当我们遇到诸如公共政策、全球化、市场竞争、去监管、垄断、效率、公平、贫富差距、数字经济等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但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这本书将1969—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讲述了经济学家的错误预言、自由市场的演进,以及由于高度推崇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断裂。
以下摘自《经济学家时刻》译者导读:
公共政策制定者往往容易成为吐槽对象。有的人在抱怨他们已经做的事,有的人在抱怨他们正在做的事,而有的人则在抱怨他们没做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如本书这样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系统性“吐槽”,也并不多见。
那么,我们不禁好奇:公共政策制定者是否一定有必要做点什么?
本书作者用数字列举出一系列美国的事实——有时候,数字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给予了我们一个日常很难关注到的结果:从寿命长短来看,1980—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增长,但最贫穷的20%平均预期寿命却下降了,同期,美国贫困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从收入水平来看,1951年出生的美国男性有75%的人在30岁时收入超过了父辈30岁时的收入,而1978年出生的美国男性则只有45%的人在30岁时收入超过了父辈30岁时的收入。而当阶层开始关乎寿命时,彰显了社会断裂的恶果,同时收入在代际递减,昭示前景晦暗,的确不能不说,美国社会进入了一种衰退。既然只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实现,那么公共政策制定者显然应该发挥作用——是有必要做点儿什么。
接下来,我们进而好奇:既然如此,那么公共政策制定者到底应该做什么?
然而,如卡尔·波兰尼这般的智者都只是说,政府的一个关键作用应该是限制变革步伐。可见,想要系统性地回答这个应然问题,绝不容易。而大师如艺术般的启示,却似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公共政策制定者有时候应该做的,恰恰不是后面的事,而是首先找到真问题。的确如此。有时候,首要的恰不在于做了没有、做了多少,而在于是否需要做、做对了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本书就太有意义了。
它铿锵道来,只为回答我们另一个好奇: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做什么?
话至此处,我也终于可以聊聊这本书为什么叫作《经济学家时刻》。如你所想,作者关注了历史长河当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公共政策制定者群体,即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家们——从1969到2008这40年,经济学家始终被曝光在镁光灯下,经历着一场极其特殊的政策制定主宰者高光时刻。这些政策不仅涉及调控税收、控制公共支出、解除监管、推动全球化等,而且包括结束征兵制、放弃反垄断法、为人命制定价格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人数从大约2000人猛增至
6000余人,不可不说浩浩荡荡。而美国虽是这场知识分子布局的中心,却非唯一。英国、智利、印度尼西亚、法国等国家很快追随其后,我们亦是弄潮儿之一。
就这样,经济学家们塑造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数十亿人摆脱了赤贫;喀麦隆人可以观看同胞在NBA(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中打篮球;印度儿童可以使用以色列药物来治疗疾病;美国人深度依赖着“中国制造”;中国人则可以吃到来自智利的深海鱼类……而如果不是放在历史长期又看上去有些无情的洪流之中,可能尚难发现这些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短期繁荣有何不妥。实际上,短期繁荣总以长期为代价——现代市场多样性与原初丰裕社会相比,带来更多的可能是深度消耗,影响的是恐难再修复的可持续性。而经济学家立足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位置,仍然在不断推进短期繁荣,从他们通过统计学这一工具认为自己对短期建立起系统性认知开始。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引领所有人拜倒在财富脚下的信仰,而它的教义通过一位位经济学家和一条条不断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以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对全人类的经济以及政治、秩序、格局、社会、行为等影响深远。正如作者所言:“米尔顿·弗里德曼像一个游离的电子一样,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举重若轻地搅动起一场思想意识的革命,他的影响贯穿整个20世纪,直到他轻轻地走了,留下了一个被他的思想重塑的世界。”
经济学家们首先让市场变得无处不在,接着便全然承包了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不间断地战斗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辩论场,基于为阶段性表现不佳的市场开出一个又一个药方。先是凯恩斯主义占据上风,可很快便从通胀加增长停滞的实践之中回归到市场自由主义,开出大幅减税的偏方,又随着里根减税政策的失败而告终。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在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反对反垄断、反对监管、为生命定价、制造出一个都想作为核心的金融游戏,并不止于此,还热心于染指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有趣的是,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多方面的不完善倒让局势变得“慢就是快”,而发达国家一飞冲天普遍落入一种难以控制的局面或许并非善缘,只能说事已至此,尤其是金融业野蛮又难自已的多样化发展。
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把自己定位在经济学家群体,至少不应该仅仅定位在经济学家群体,无论他是坚定的市场自由主义追随者,还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守者。我们所处的当下世界,虽然仍然秉承着市场经济这个人类伟大的发明,但是市场经济中的人相当鲜活:不仅可能生活在金字塔尖,还可能生活在金字塔底;不仅注重金钱,还注重机会;不仅要满足生存层面的数量要求,还要满足生活层面的质量要求;不仅受到数字激励,还受到心理影响;不仅拥有理性思维,还时不时受到感性支配。而这些,都游离在“经济人”假设之外,并以各种表现形式和不同力道拉扯着与“经济人”之间的纽带,既可能游刃有余,又可能一触即发。
然而,我们已经经历经济学家们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高光时刻,人类已经被更加紧密而广泛地联系到一起,尽管仍然有不同的文化根基,但也已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倾向于认同经济学家所建立的各种通则。经济学的每一条原理,都很难不关乎全人类的抉择;每一次抉择,又很难不关乎全人类的命运。无论各地是否陷入了如本书作者基于美国事实所反思的那一种“经济学家时刻”——政策的转变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并将利益集中到少数富豪的口袋里面,辐射不同地缘的公共政策制定者们如果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都已难独善其身,更加难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一如新冠肺炎和埃博拉、一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一如冰山消融和物种减少,也一如贫富悬殊和代际差距、一如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一如设租寻租和利益集团,都在不断地挑战着我们的想象力,同时又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细节。
《经济学家时刻》一针见血的40年故事,让我们立足于这个不断挑战人类想象极限却依然即将要过去的2020年,对西方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对东方,更对整个世界,翘首以盼。
《经济学家时刻》
原版书名:The Economist’sHour:False Prophets,Free Markets,and the Fractureof Society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作者简介
苏京春:
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译有《经济奇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通往衰败之路》等。
END
编辑|思洋 校对|坚果 视觉|牛小伟